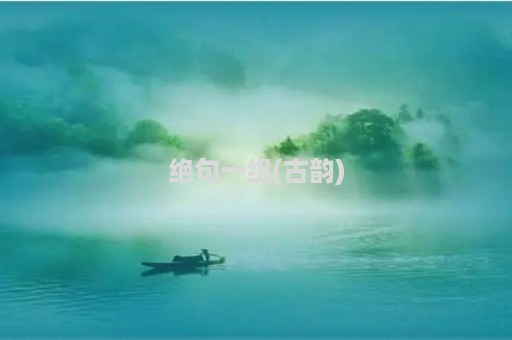记得从前,小学语文课本里曾有一则《郑人买履》的故事。说古时候有一个郑国人,要买一双鞋子,在家已经量好了脚的尺码,却把它放在了座位上。等到了集市上,鞋子已经拿到了手里,才想起自己忘带了量好的尺码,于是他又返回去取尺码。可等他再次来到集市上,集市已经散了,卖鞋的也早已走了,他因此没有买到鞋子。据说该故事是《韩非子》里的一则寓言,它讽刺了社会上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循守旧而不懂变通的人。
这里的“尺码”明显就是郑人量好的脚的尺寸,鞋子的大小应该是由脚的尺寸来决定的。“尺寸”即尺和寸,一尺等于十寸,生活中它通常就是用来量长短的。“脚”长在人们的“身上”,即身体的一部分。所谓“身上的尺寸”,其实就是以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动作来确定事物的基本情况。这时候的“尺寸”应该说就不在限于物体的长短和大小,它还应包括事物的粗细、高低或深浅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体是人们最熟知也最方便的使用单位。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乡下老家的上辈人都在熟练地使用着身上的尺寸,而且他们交流起来也显得非常地亲切和自然。记得从前我跟着洗衣服的奶奶去坑里洗澡,有人问水多深,靠边很浅,我就说“脚脖深”。可往里稍走走,就变成“腿肚子深”了。如果打个狗泡泡,还是“没膝深”;再往前一扑,也就到了“大腿深”。往往到此处,奶奶就不让我朝里走了。有时秋天跟着父亲去沤麻或捞麻,父亲常常要下到坑里面,“齐腰深”的水往往冰凉冰凉。
当然,有时尽管大人和小孩子的说法一样,但水的深浅度显然是不同的。关于这一问题,教材里《小马过河》的故事说得很明白,小松鼠的话不可信,老牛的话也不可信,因为比较对象不同,结果也就大相径庭,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自己实际去试一试。但乡人们不是小马,他们对于家乡的水塘都十分熟悉,深浅也了如指掌,哪个地方“穿胸深”,哪些地方“没顶深”,他们一般都能直接用身体的相应部位来表示。
当然,讲水的深浅,通常是以水平面为基准向下来说的。如果说田里的庄稼,则又是从地面往上来说的,自然就转化成了“脚脖高”“腿肚高”“齐腰高”“穿胸高”和“一抹高”了。“一抹高”就是身长加上手举起的高度。那些年我们小朋友在地里割草,从开春挖荠荠菜时小麦的脚脖高,慢慢地到了小麦拔节后的腿肚高,很快就会到了抽“乌麦”的没膝高。当秋天到来的时候,无论是芝麻还是棉花都能长到穿胸深,玉米和高粱都超过或远远地超过了“一抹高”。
事物是纷繁复杂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形容事物大小的时候,人们用身上的尺寸来表达,很多时候就会显得既形象生动又妙趣横生。有时说一个极小的事物,小得像针尖、如芝麻粒,则常常说成小得跟“指甲盖儿”一样;有时说一个地方不大或难以立脚,则说成“巴掌片”大的小地方,甚至说成连个“巴掌片”大都没有,让人如何搁脚呢?同样是一个嫩瓜扭儿,若是不想让摘就说还没有“拳头”大呢;若是可以吃了,则说长得跟“拳头”样儿了,不能算小了。
我记得爷爷爱吸烟,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买成盒的香烟,他就把我写过的作业本一折叠,用两个手指一比划,撕成了“二指宽”的纸条,裹成喇叭筒,装上揉碎的烟丝,从地上捏起一根柴草,引火来吸。冬天,父亲给我们拧草鞋,木底都削成了三四指厚,走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响,但内里真的很暖和。母亲纳鞋底取样子,先做个大样,常常是用手一拃再加一“揆”。当时只听母亲说gui,具体是哪个字,我至今也搞不清。这“揆”大致是拃后再握拳向前一摁,到底是多少,看起来只有母亲最清楚。
村里村外,当年长有很多树,在形容它们的大小粗细时,人们的说法则更多。老粗的,我们都知道称“合抱之木”。不过,当时我们好像都叫它“俩搂粗”,有时还说成“俩搂也搂不住”。往下自然是“一搂粗”,再往下就该论“把”了。一“把”通常又说成一“拃”,也就是手指伸开之后,从大拇指指尖到小指顶端之间的距离。接下来,就是一“掯子”。“掯子”是两手的拇指和拇指与食指和食指对接成圆,圆周的大小便是。
这掯子除了说树的粗细大小之外,还通常用作形容长条形的东西。爷爷当年是个老瓜匠,瓜地里常常附带地点种些豆角。爷爷摘豆角的时候,一般是论“把”,有时撞得整齐,再用麻皮子扎起来,也说成粗哏哏的一掯子。再细再小,就是一“握”了。“握”大致是手掌的长度或拇指与中指的交合。一“握”通常用来形容 *** 器具的木材,譬如木掀把、铁锹把或抓钩把等等。再小是用拇指套食指来回比划了,细到最后就说成了跟“头发丝”一样。
至今犹记,当年“把”的使用最为普遍。抽蒜薹、拾麦穗常常是弄得一把,先放在地头或田埂上,最后一把一把地聚集到一起,凑成一大“掐子”。“掐子”是大拇指朝上四指朝下两手合拢而成。收割庄稼的时候,右手拿镰刀,左手“把”住庄稼稞儿,割够“一扑子”再往身后一放。“扑子”大致就是用胳膊一绕或一圈。有时在地里拾遗漏的花生,或在场里捡散落的黄豆籽,通常也都是一把把地装在事先准备的口袋或布袋里。
天热的时候摘绿豆,我们时常挎着个篮子,或弯腰或蹲在绿豆秧里,此时阳光正毒辣,摘一把绿豆擦一把汗,抬头看看前方,总有一种眩晕的感觉。现在想想,“一把绿豆”黑黑的,是实实在在的,容易理解;这“一把汗”就不太好理解。据我所知,擦汗时手里已经握有一大把绿豆,脸上痒痒的,来不及放下,就便用握住的拳头绰了绰。下地摘棉花最痛快,两手同时下去抓,一抓就是两把。妇女们还将衣下襟拉在胸前一兜,这种做法叫做“褓”。“褓”虽然不属于身体的部位,但它和人们的胸怀联系非常地紧密。
土地下放后,我家养过牛和驴,在喂它们的时候,有时父亲正忙,他就让我给它们捣一槽。初开始父亲安排我说:“先掬上两掬子麦秸在水缸里淘一淘,再从旧五升斗里抄两抄子麦麸撒上,然后用拌草棍捣匀。”“掬子”有些类似于“掐子”,手形和“掐子”基本相同,它只是没有“掐子”把得紧,要比“掐子”掬得的东西多。“抄子”也是手部动作,它是五指并拢,做成一个勺子状来搲东西。后来草料足的时候,“抄子”就变成了“捧”了。相信“捧”大家都比较熟悉,它是五指并拢两手对在一起做成瓢的形状。
很多时候,现在想起来还好笑。我们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正常情况下,胳膊是没有大腿粗,但大腿又没有腰粗。可有时候人们形容一个人长得细脚伶仃的,说她的腰还没有别人的大腿粗;当形容一个人粗实的时候,则又说成胳膊比别人的大腿还粗。记得当时就有一词叫做“五大三粗”,“五大”一般是指双手两脚再加上脑壳,“三粗”是指腿、腰和脖子。“五大三粗”在以前是个褒义词,据说手大能聚财、脚大走四方、头大能做官。不说这些,最起码它也是身强力壮的象征。
要说这人身上的尺寸,那是绝对不能少了“庹”(tuo)和“步”的,它们是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最方便也最常用的。先说这“庹”,据《字汇补》一书中说:“两腕引长谓之庹。”通俗地解释,它一般是指一个成年人两手向左右平伸所得两手指最尖端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五尺”。想当年,垒墙头、打绠绳、估木之长短等,乡人们都是按庹来计算的。有人说一个人的“一庹”基本上就是他的身高,但身高很难颠倒或变通,通常只能用来丈量直立的事物,平倒或横卧的东西就无能为力了。
关于“步”,荀子的《劝学篇》里有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古人常常把走路时两脚尖的距离叫做“跬”,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单步”或一小步,也称作“止”;两“止”即两小步,为一大步或一“步”。“步”和“庹”都曾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里写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钩心斗角。”当然,这里的“五步”和“十步”是用来形容阿房宫楼阁密度之大的,并非就是通常所说的具体的“步”。
“步”作为计量单位,历代不一。周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则以六尺为一步。记得当年父亲都叫一步为“一弓”,听话音好像是五尺的样子。那时候,用“步”丈量的多为土地,譬如宅基地、自留地和“分片包地”。“分片包地”是指包工干活或分片捡拾土地里遗留下的作物和食物。当时生产队高温积肥,拉土填麦草,大路两边堆成的檩子状好长好长。量土方的时候,人们通常就是来回步步长短、用腿量量高低、用眼看看宽窄,一折合就成了。
据说,古书上还有“五尺男儿”和“三寸之舌”的说法。长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相传我们的祖先通常是布指为寸,布掌为尺,舒肘为丈,到秦始皇才统一了度量衡。因此,“五尺男儿”也常常说成“七尺男儿”,它一般是指那些拿得起放得下、有血性能挺直腰杆的人。男儿不展凌云志,空负天生七尺躯。抗战英雄陈辉有诗云:“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三寸之舌”语出司马迁的《史记•平原君虞列传》,“胜(平原君赵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三寸之舌”又称“三寸不烂之舌”,它多用来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辩才好。“不烂”应该是指舌头的转绕润滑,说话拐弯抹角曲折有致,不漏声色或痕迹。
“身上的尺寸”是那个古朴而又简陋的农耕时代的特有印记,它虽然大都是一些估量或约摸,不像现代科技可以上升到纳米微米那样精细而准确,但由于人们使用频繁、操作熟练、磨合有度,反而常常又会表现为自然合理、简便得体、实用而又颇具艺术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切的一切都在围绕着人们身体的舒适迈进,在时间和空间或物质和精神等方面,人们始终都在做着各种尺寸的伸缩与调适,正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